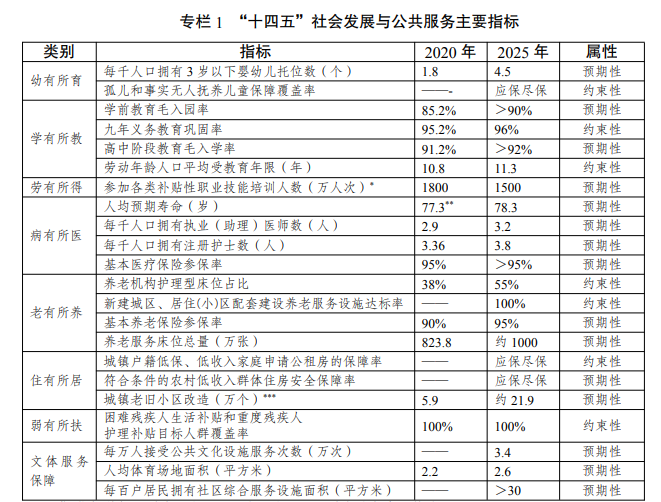4月5日,清明时节,湖北省赤壁市羊楼洞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一早就迎来了第一批祭扫者。
 (资料图)
(资料图)
这个位于湖北省南端的村落地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交界,周围群山环绕,由于前一天下过雨,四周山顶氤氲着白色的水气,林中传来清脆的鸟鸣。
青山环抱之中,140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此长眠。
张祥忠烈士后代4月5日祭奠英灵。
祭扫的过程中伴随着呼唤和低泣,近百位扫墓者中有冉性初、周学山、卢占富、吴海廷、张仁金、张祥忠、傅长学等7位烈士的亲属13人,他们分别来自湖北、河南、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其中5位烈士的亲属都是首次来到烈士的坟前祭扫。
芦占富烈士侄孙女芦凤云说:“如果不是余叔找到我们,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爷爷了。”
卢凤云说的余叔,就是赤壁市公安局退休民警余发海。从2005年开始,余发海用了18年时间为烈士陵园中的140位烈士寻亲,到今年清明节前,已经找到了126位烈士的亲属。
山中的142座坟茔
羊楼洞烈士墓群2014年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余发海是一位传奇警察,他出生于1951年,曾经是一名孤儿,后被人收养,他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人民警察。33岁时,他破获一个牵涉湘鄂赣豫四省的伪造户籍案,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等功。
2003年,52岁的余发海因感染“非典”引起肾衰竭生命垂危,进行肾移植后重获生命。出院后,余发海需要每天服用抗排异药物,每隔几个月还要到医院复查。2005年,他被公安局调离一线,去做公安史志的整编工作。
就在那一年,他接到一项任务——“有人在羊楼洞村发现一片烈士墓,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你去考察一下。”
几经辗转,余发海在羊楼洞村附近老营盘种满茶树的山坡上找到了这片墓地。
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大雨滂沱,山坡上长着一人多高的茅草,风吹过现出一排排圆头的石碑,就像一排排埋伏在草丛里的战士,山林沉寂无声,我却仿佛听见他们的呐喊。”
走到近前,墓碑上满是青苔和泥土。余发海扯了一把野草拭去污物,一片片文字开始显现:“……抗美援朝烈士……志愿军烈士……”他顺着山坡绕圈,慢慢数数,一个、两个、三个……一直数到142个。从碑文看,这些烈士中有步兵、空军、铁道兵、炮兵,有战士,也有班、排、连、营干部,年龄从18岁到52岁,部队番号涉及31个军37个师,籍贯涉及全国24个省、118个县市,有朝鲜族、蒙古族、苗族、彝族、满族、壮族、土家族、彝族、阿美族等9个少数民族,其中还有3位女兵。
余发海非常震惊,心里翻滚着无数个问号:“怎么会有这么多志愿军烈士?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亲属知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他下定决心,要像侦破一个个疑难案件一样,破解这142个谜团,给这些为国献身的烈士一个交代。
一个都不能少
余发海到各个省区档案馆查到的烈士资料。
这些烈士为什么来到这个鄂南小镇?余发海很快找到了答案。
他查阅《蒲圻县志》(赤壁市原名蒲圻县),在“大事记”中看到了一段记载:1951年6月21日,羊楼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正式接受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至1953年7月,共接受伤病员3100人,治愈2700余人。
随后他又查到《赤壁民政志》,其中更明确记载:第67预备医院因救治无效而牺牲,就地安葬的有133人,均追认为烈士。
随着资料的增多,历史浮出水面:抗美援朝时期,因京广铁路在羊楼洞附近建有一个赵李桥站,部队在此设立了第67预备医院,朝鲜战场上负伤的战士运送回国救治,有一部分通过铁路运送到此。1956年3月医院撤销,医护人员分散安置。
这些烈士无疑就是因救治无效而牺牲的志愿军伤员。那么问题来了,羊楼洞村有142个坟墓,其中有姓名有碑文的137个,而《赤壁民政志》记载的是133人,为什么?而且,墓地中3个坟墓没有墓碑,还有2个只剩空穴,又是怎么回事?
余发海想要解开谜团。
经过比对,在《赤壁民政志》中,墓区4排9号张学年、5排9号张云超、6排12号刘宜斋、7排12号张仁金烈士没有找到记载,这是什么原因?余发海把重点放在当年编写《赤壁民政志》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身上。通过寻找,他找到了当年《赤壁民政志》执行主编——八十多岁的李昌树先生,李昌树拿出了《赤壁民政志》原稿,发现了被遗漏的4位烈士的简介,而且都在一页纸上。据此分析,也许是当年打字员遗漏了一页稿纸。后来通过查阅各地《烈士名册》及民政部门调查,进一步核实了4位烈士的身份。
后来,失踪的颜生、罗正新、曲同庆烈士的墓碑也在离烈士墓群不远的两口水塘边上找到。
这样,烈士的总数就有140位,那2个空穴里是谁呢?他突然想起一位曾在羊楼洞茶场当过保卫科长的退休老公安李时楷。据李时楷回忆,曾有2位农场干部去世后就地安葬在烈士墓里。通过查阅羊楼洞茶场档案,证实了他的说法。在羊楼洞村76岁的老队长许立君的引导下,余发海在离烈士墓园不远的一片荆棘丛中见到了欧阳南、王荫璋同志的墓碑。后来得知,1982年当地镇政府维护烈士墓园时,发现这2位同志的坟墓,因其不属烈士,就将其移到烈士墓群外面了。最终确认,墓群中实际有烈士140人。
2006年,余发海将考察结果汇集成《关于羊楼洞142烈士墓群的考察报告》。2006年3月1日,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曾求腾少将到烈士墓群考察。余发海清清楚楚地记得,曾将军围着墓地转了几圈,连说了三次“我们的战士真伟大”。随后,总参戚建国上将、著名军旅作家魏巍等先后前来考察、祭扫。烈士墓群也逐渐受到各级政府重视,政府多次投资修缮墓园并修建道路,烈士墓群正式命名为“羊楼洞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并成为各单位和各级政府的红色教育基地,很多人来到这里祭扫。
100封寻亲邮件仅收到8封回信
革命烈士纪念碑。
2006年,赤壁市公安局与羊楼洞结对扶贫,余发海成为3位驻村扶贫工作人员之一。余发海说,临行前公安局领导特别叮嘱:“你不要管其他工作,专心做好你手上的事情。”
2006年清明,他根据烈士墓碑上的籍贯信息发出了100多封信件,这些信件大部分是寄给烈士原籍的村委会、人武部、公安局、民政局等单位,请求他们协助调查,找到家属。
可是整整等了一年,除了有30多封信被邮局贴上“査无此地此人” 或“地址不全,无法投递”的条子退回,其他大部分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一年间,他只收到8封回信。在回信里烈士亲人的讲述催人泪下,他们大都不知道烈士牺牲在羊楼洞,有位妻子甚至为烈士守候了几十年。这些讲述更加激发了余发海,他从此踏上为烈士寻亲的漫漫长路。18年来,他的行程上万公里,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为什么很多烈士的家属当年没有得到消息?余发海找到当年第67预备医院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当时伤员从前线千里转运而来,很多伤情较重,已经说话困难,有的还带有方言口音,有的在登记时还是报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部队番号,医院护士豋记时难免出现一些讹误。伤员抢救无效身故后,医院会通知原部队追认烈士,给家属寄发《烈士证书》,因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战争时期部队大范围调整,邮政体系也不健全,所以多有遗漏,有的烈士家属收到了通知,由于路途遥远祭扫不便,随着老人故去,后辈也就没了消息。
第一位烈士亲人浮出水面
余发海为每位烈士家属赠送《英雄烈士保护法》。
到2006年,烈士逝去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启动寻亲并非易事,首先各地的行政区划经过多次变动,省、市、县、村的名字、归属都有变化;其次随着时光流逝老人凋零,认识烈士的人也已不多。
余发海多番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寻找方法:先去各个省查烈士的详细档案,然后再通过公安系统户籍信息查找,再通过当地志愿者、媒体发动群众一起寻找。
山西介休的温秉仁烈士的弟弟温秉根是余发海找到的第一位烈士家属。烈士墓碑上的地址是山西休县四区东村,经山西介休市民政局查询得知,现为义棠镇北村。该县烈士名录中并无温秉仁的记载。2006年清明后,余发海按义棠镇北村地址给村委会去信,很快找到烈士的弟弟温秉根,当时温秉根已经73岁,温秉根给余发海打电话说,只知道其兄入朝参战,后来几十年没有音讯,父母多次查访无果,今得知牺牲安葬在羊楼洞,心情很沉重,希望前来祭扫。
找到一位活着的“烈士”
羊楼洞烈士墓群第10排10号墓属于胡金海烈士,碑文上写着——胡金海烈士:四川江津县金岗乡长城村人,1949年长沙起义6月入伍,21兵团战士,1953年12月牺牲时27岁。
2007年2月,协助余发海寻亲的志愿者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胡金海烈士的家,可接待他们的却是胡金海本人。大家大吃一惊,这位“烈士”怎么还活着呢?
2007年8月的一天,胡金海给余发海打来电话,说他决定要来湖北羊楼洞“给自己扫墓”。三天后,胡金海带着江津县人武部给他出具的退役复员证明从重庆赶到了赤壁。在羊楼洞烈士墓地10排10号墓前,胡金海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碑文上的姓名、籍贯、部队番号、入伍时间和年龄与他完全一致。他百思不解,安葬在这个墓里的战士又是谁呢?
余发海看到,胡金海从随身的黄书包里拿出一只塘瓷缸和一瓶白酒,双膝跪在墓前,一边将酒倒在地上,一边流着泪说:“战友你是谁啊?我好好地回来活到了退休,你牺牲了55年却至今不知姓名。”沉默一阵后,他站起身来,走到每一个墓碑前,依次敬了一个军礼。
离开墓园前,他对余发海说:“拜托你查到这位战友的名字,找到他的家属,找到了一定要告诉我。”
那天在墓地旁边的茶山上,胡金海讲述了参加甘岭战役和金城阻击战的经历。他回忆起,上甘岭战斗异常残酷而激烈,有一次在冲锋途中,他发现身边躺着一位受了重伤倒下的战士,敌人的燃烧弹将他的衣服烧烂了,浑身皮开肉绽,他看到这位伤员动了一下,胡金海就将自己的军装脱下,盖在了这位战士身上,然后继续冲锋。
那时候,军装左胸口袋上方有一块布牌,正面印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反面有每个战士的姓名、年龄、部队及籍贯地。他猜测,可能是这位战士被送到后方医院,牺牲时,医院根据军装上的布牌将他误认为胡金海了。
2013年2月,上甘岭老英雄胡金海去世了。余发海又想起他生前的托付。要找到“胡金海烈士墓”里无名烈士的身份,唯一途径是去查原四野入朝参战的部队原始军档。2021年3月16日至18日,他在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帮助下,去南部战区政治部査阅了安葬在原蒲圻县羊楼洞的烈士原始档案,终于发现一位牺牲后安葬在羊楼洞村的烈士,名叫傅云贵,他就是“胡金海烈士墓”里的那位无名英雄。
年龄最小的战士覃汉坤
烈士墓群里,年龄最大的是杨玉春烈士,四川富顺县大山铺乡人,1946年7月入伍,三野六纵2营5连战士,1954年8月10日牺牲,时年52岁。年龄最小的是覃汉坤烈士,碑文记载:覃汉坤烈士,1934年生,广西贵县三区覃塘龙岭人,1951年入伍,45军军部文教干事,1952年10月17日牺牲,时年18岁。
2007年5月,余发海乘火车去贵港为覃汉坤烈士寻亲。碑文上的三区现为覃塘区,余发海转乘班车去了龙岭村,村里无人知道覃汉坤的名字。后来碰到几位80岁左右的老人,其中一位老人把余发海带到覃汉坤家的老宅,房屋早已荒废,有人说他二哥曾在广州教书,如健在可能有80多岁了。余发海想了个法子,把碑文资料写给当地派出所,拜托民警帮助打听亲人下落。
余发海回家不久就收到了贵港市公安局户政科的回函,函中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覃汉坤的二哥覃汉珍在广州找到,并提供了其子女的电话号码。
联系上覃汉珍,覃汉珍老人老泪纵横。据他介绍,覃汉坤1951年还末满17岁时,在学校和两位同学一起瞒着父母报名参军入朝作战。临行前,覃汉珍夫妇在火车站找到了他,他对哥嫂说:“好不容易全国解放了,美国佬又发动了侵略战争,我要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走了,你们不要告诉父母,如果我牺牲了,就把你们的第一个孩子过继给我。”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覃璐玲,如今已从广州地税局退休。来羊楼洞祭扫时,她说:“叔叔是烈士,烈士不能没有后代,父亲按叔叔的遗嘱把我过继给叔叔了,我就是叔叔的女儿……”
从一个余发海到一千个余发海
为140位烈士寻亲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余发海成了名人。他先后成为2008“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候选人、2012央视“中国好人”。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志愿者组织加入寻亲的队伍。
2007年1月24日,余发海应邀去华中科技大学作了一场为志愿军烈士寻找亲人的报告,该校师生备受感动。离校时,该校团委要余发海将还没有找到亲人的烈士资料提供给他们。当年寒假,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自愿报名,按地域分工进行,开展“为英烈寻亲”活动,发动各自的社会关系进行寻找。在超过1000名同学参与下,活着的“烈士”胡金海、田炳义烈士的女儿田茹妮等22位烈士亲属先后被找到。
余发海的年龄越来越大,赤壁市义工联盟在当地政府指导下于2021年4月成立了一支“余发海烈士寻亲志愿服务队 ”,招募了23名志愿者协助他开展工作。近3年来,服务队根据余发海提供的资料找到了3位烈士的家属。经他们联系山东青岛市蓝海救援队、河南固始县让爱回家志愿者组织也找到4位烈士的家属。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及找到的烈士家属也都纷纷参与寻亲。
现在,全国的烈士信息已经可以在退役军人事务部主管的“中华英烈网”上查询,年轻的志愿者使用网络手段寻亲效率也更高,烈士的家属以更快的速度被找到,更多的家属来到羊楼洞祭扫英烈。
截至今年清明,余发海的寻亲名单上还剩下最后14位烈士。他告诉记者:“对于我来说,找到一个烈士亲属就像是破解了一个案子。我非常高兴,18年的寻找即将画上句号。”
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jp.jiupai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