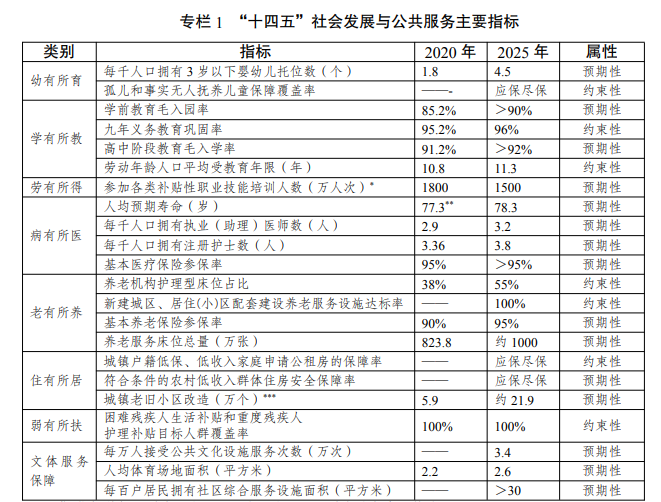五千字左右的be,有糖,但不多。
 【资料图】
【资料图】
夕绝望地站在墙边,将自己的画一张一张地丢进燃烧正旺的火炉里。她看着那些跃动飞舞地火星子,注视着一层层弯曲变黑的画,看见漫长的岁月以怎样的方式与她作别。
她巴不得岁月可以如火焰焚烧般与自己分别,懊悔自己终究是错付一场,倒不是错付了人,实在是错付了一场岁月,一道无始无终无形的圆。想到这里,她胸口揪心的疼。
夕入神地焚着画,还以为是风吹动了房门,回过神来,手中剩下的画已被径直走来的男人夺去。男人看着画,又瞅了瞅炉子里的灰,不无可惜地说:“烧画做什么?怪可惜的!”
“要你管!”夕白了他一眼,伸手便要将画抢过来,这一来一回,男人倒连画带人搂在怀里,笑说:“怎么,不惜投怀送抱也要烧了这些画吗?”
“再不给我,连你一起烧了。”夕倚着男人,眼睛还盯着燃烧的火炉。
“告诉我理由,我便让你烧,烧了我也可以。”
“博士,你不会明白的。”
博士松开了怀抱,将手里的画还给她说:“你不说,我永远也不会明白的。”又说,“这屋子里其他的画,送我吧,也比烧了好。”
“你不懂画,也不想懂。”夕性子多少乖戾,自己的画宁可毁了也不送人。
“我想懂你。”
博士临走的时候撂下这样一句。
夕烧了手中的画,对着炉火喃喃:“你真的能懂我吗?”
夕出了自己的画室,一路来到罗德岛舰桥的甲板上,博士常常会在这里远眺,此时他果然也在这里。他迎着风望着落日的方向,像一尊等待离人的雕像一动不动。可惜尽头没有离人,离人是身后伊人。
博士察觉到夕的身影,他向来对她的动向敏感,就像脑子里装了雷达,即便是人山人海,他也能一下所定夕的位置。
“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博士说。
“这是大姐喜欢的。”夕的脸上波澜不惊。
“你不觉得这景象的壮阔吗?你分明也画过这样的景象。”博士记得夕画过的每一张画,他找她看那些画,死缠烂打,求也好,威胁也好,吓唬也好,全然不顾及自己指挥官的尊严。他觉得只要了解了夕的画,就能进一步了解夕的内心,他满心期待自己能走进去,痴心得像个孩子。而事实上,博士在夕看来就像个孩子。
“画过又如何,这天下的景致我已经腻了烦了。”夕说。
“景致会变的,风沙侵蚀,潮涨潮落,四季轮转,某一天,这片荒凉也会成为绿洲,我见不到,但你能见到。”博士清楚这个世界在日积月累间总会发生变化,量变到质变,他只是可惜自己寿命有限,见不到那些质变的奇迹。
“这些变化,我很久以前就见过了。”夕看着博士期待的样子,笑了。
甲板上的对话对博士而言是失败的,无论他藉着天地规律展望怎样的变化,夕的表情都是冷淡的,她见过了,她见过了,无论他说什么,她都说见过了。
“那你见过七眼八手九脚的兽吗?”博士最后用编造的怪物问她,想着这总不能也见过了吧。
“没见过。”
夕终于说了没见过,博士却一时语塞,编造开始的时候,再多的美好畅想也不再有意义了。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可他对夕的爱是真的。
“你对我,腻了吗?”博士不再远眺,转过身看向一旁的夕,他眼里的她明眸善睐,心思细腻,他爱她爱得心里火烧火燎,但即便他的心成了太阳,他也实在是冲不破她俩之间那堵无形的,名为“你不懂”的墙。
“还没有。”
博士以为自己抓到了破绽,对夕说:“我爱你。”
“有意义吗?”夕的眸眼透彻的仿佛一面空玻璃,“这份爱,不就是一坛炉火吗?爱能把你我一起烧尽吗?”
博士无法回答夕的问题,他甚至没有听懂这个问题到底指向什么,是想考验这份爱的坚贞,还是说想考验其他。
后来,博士一宿没睡,辗转反侧的想这句话的意思,第二天,他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兴奋地冲进夕的房间,却发现房间已经收拾的干干净净,心中的佳人早失去了踪影。
“夕呢?夕去哪儿了?”他气急败坏地去质问可露希尔,可露希尔只给了他一幅画,说是夕留给他的。他问她还留下什么了没有,可露希尔摇头说没有了。
博士当场打开画一看,这是夕新画的作品,一坛火炉,燃烧的火炉。
那天,博士独自在办公室掉眼泪,他恨自己窝囊,蠢笨,看不明白夕的变化,听不明白夕的话语。他是真真切切地爱她,巴不得每天醒来就能看见她,但哪有爱情是求来呢?哪有爱情是靠着一方哀求另一方就能得到的呢?世间又哪有你爱她,她就必须爱你的道理呢?
可博士心里觉得夕是对自己有感觉的,否则也不会留下这幅画。他把那幅画挂在卧室的墙上,闲下来就瞧它,白天瞧,晚上瞧,总想参悟些什么出来。他兀自把这视为夕对他情意的考验,赢了,便能赢了。
夕独自去了尚蜀,一天夜里,她坐在大姐令的小楼别院里饮茶。
“夕妹妹,你心事很重。怎么连画也不画了?”令着实喜欢自己这性子乖僻的妹妹,生的漂亮,绘画的功夫又了得,无论哪个时代都算得上是举世无双的女子,除了一点——总喜欢将自己关在画里不出来。如今倒好,夕弃了画,索性也不关着自己了,但在令看来,这还不如她以前咧。
夕便将博士的事情说了出来,令听后,忍俊不禁。
“妹妹,你喜欢他?”令问。
夕既没点头,也没摇头,说道:“别说喜欢了,就算是爱,又有什么用呢?他不过是个普通人。”
“你瞧不起他是凡人吗?”令装着疑惑的样子说。
夕白了一眼说:“姐姐当真不懂我的意思吗。”
“唉,”令叹了口气,倒了杯酒说,“我知道妹妹的意思,可是这又何妨呢?今宵有酒今宵醉。”
“姐姐是洒脱,我可不行。”夕从腰间抽出笔来,在空中挥斥几番,一幅月夜对饮图跃然空中,“这世间有什么景,什么情是我没画过的呢,山水田园、虫鱼鸟兽、悲欢离合,所见所想,经我手皆可留存画中千万年不朽。我总以为,会有全新的存在让我画,但几千年过去了,你我都看见了世代的变化,那些普通人心心念念的进步,在你我眼中终究不过是新装又把旧戏唱。强夺的依旧强夺,和善的依旧和善,好战的依旧好战,呐喊的依旧呐喊。这些,我都画过千万遍了!”
“但你的画可以让一切都变得美好,你可以创造光怪陆离,经久不衰的世界。”
“经久不衰的世界?一把火,大梦初醒。”夕随手一挥,月夜对饮图烟消云散。
令明白妹妹的意思,但她想,如果妹妹真的全然放弃了,那她为什么不拒绝博士呢?
“那你为什么不拒绝博士,反而留一幅画给他呢?你这人走了,画却留下,倒是有欲擒故纵的嫌疑。”
夕却没有狡辩,她其实爱他,所以不觉得自己错付了人。她放在腿上的左手捏起了旗袍的褶皱,咬着下嘴唇说:“他如果能懂,我或许能答应他。”
“他懂了吗?”
夕摇摇头:“他不懂,他的展望在我眼里不过是重新在旧的草图上换只笔画新图。”
“可是他爱你吧,即便他不懂,即便他的展望在你的眼里是重蹈覆辙,他还是选择爱你,爱你这件事情,难道也是重蹈覆辙吗?”
“他爱我,是我自己的重蹈覆辙。姐姐,你会和一个普通人恋爱,成家吗?他会渐渐的两鬓斑白,身体衰老,皱纹横生,可我们呢,我们一直会这个样子,青春永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人死去,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不想这样,我不想这样!”夕有些激动,很快又冷静下来,“你说得对,我就该拒绝他,我就不该让他以为我在欲擒故纵,我不想看着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不想把他留存在我画里,终将朽坏的,爱情也好,人也好,都是命。”
夕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地扎进夜色里。
令不想追她,她知道这是夕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她也知道妹妹口中的话语所描绘出来的绝望图景是怎样的梦魇,她可以选择逍遥不去想,但妹妹不行。她只能看着妹妹渐行渐远的背影,将一壶酒全然饮下。
博士再见夕的时候,是在一个发烧的夜晚。他躺在床上,汗流浃背,为情所困,血液在百骨间奔涌,他不解画中的真意,翻遍了各样的古籍画册,就差去云雾缭绕的蓬莱寻仙了。
朝思暮想之间,见到心心念念的长发女子从窗外飞进来,他一度以为自己是见到了死前的光景。
“我要死了吗,夕小姐?”他虚弱地问。
“你只是发烧了。”夕坐在床边,掌心贴在博士的额头,“睡一觉就好了。”
博士撑着起身,双手握住夕的右手说:“告诉我,告诉我那火炉的意思吧,求你了。”
“告诉你,你就能懂吗?”
“告诉我吧,我能懂的。我知道你爱我的,不然你不会回来。”
只是刹那,夕萌生了让博士在此刻死去的念头,她想这男人若是因着病带着对她的爱死去了倒好,反正一秒钟和一千年在自己这里都没什么差别,权当这男人也算自己的同类,自己也好为他哭一场。
转念夕又丢了这念头,她将博士床头的药冲泡好端给他,一勺勺吹凉了喂他喝,她受不住揪心,便不放他死。
“喝了,喝了就好了。”
博士喝了药,又问她画的意思,她本来见他就是为了作别,告诉他便也无妨:“博士,这火炉是画的,但这画布是纸的,我画的火炉,终究是要烧了这画的,是自取灭亡。就和这爱情一样,你对我的爱是这画纸,我对你的爱是这火炉,我终究是要烧光你的,你却烧不尽我。”
博士若有所思,说道:“所以,所以你当初在甲板上问我,这爱能把你我烧尽了吗?”
夕没有回答,又说:“博士,你就好好休息吧,既然知道我爱你,就好好睡一觉吧。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可以再说。”夕见博士憔悴,便将那些别离不爱的话藏起来,等他康复再说好了。
博士康复得很快,不出两日便活蹦乱跳,饭量恢复。他洗了澡,换了行头,迫不及待地去找夕,生怕夕哪一日又不见了。
最后,博士在夕的画室找到了她,那时她正坐在窗前欣赏绽放的桃花。
“你是不是当时还有话没有告诉我,你不会是为了说爱我才回来的吧。”博士鼓起勇气,他害怕那些夕藏在爱意背后的隐句,但隐句本身又勾起他无穷的好奇。
“是啊,我本是来和你告别的。”
分明是早就预想到的事,自博士明白了那画中的意思,他就知道夕的心意,然而早有防备的心依然被夕的回答刺透了。他攥着拳,指甲深入皮肤渗出血来,不甘心地问:“难道我爱你,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你就不可以陪在我身边吗?”
“不可以,我和你不一样。你能不老不死吗?你能看见我的绝望吗?我们爱错了人,没什么好难过的,没什么好可惜的,甚至我们能错过都是你短暂人生中的幸运!也是我的幸运。”
“你太不讲道理了。”博士沮丧地说。
“我何时讲过道理,不然我为什么起先从不送画给你。”夕神情落寞地嗤笑说。
“好,夕,我不爱你。我不爱你了!你可以留下了吧!”博士逞强几句,心却在抽痛。他背过身,“咚”一声关上了门。
三天后,夕又一次离开了罗德岛。她不再作画,只是后来靠着回忆又拾起笔,画了几次博士,有哭有笑的样子,站着蹲着的样子,然画完不出半日便尽数烧了。她想自己的岁月冗长,戒一个男人,也不过是大梦一场。
不知又过了多久,夕听闻了博士年迈病逝的消息,得知这个男人倔强地终生未娶,她兀自觉得自己是个可恶的女子,在看见博士墓碑的时候,她更加确信自己的残忍。
那个痴情的男人在墓碑上竟写着——夕小姐之爱人这样的称谓。她察觉到一股突然的暖流从脸颊划过,她羡慕他短暂的人生可以将漫长的绝望分割出细小的喜悦来,也可以傲慢的单方面表达自己的飞蛾扑火的爱情。她抬起笔来,重重地击打在岩石上,笔杆咔嚓折成两段。
夕已经再也不需要画什么了。